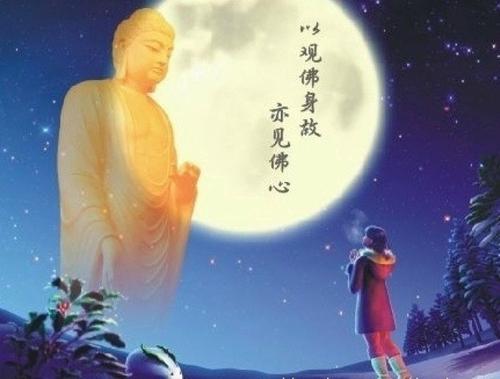生命似乎是偶尔的一粒种子,就这样飘落人间
秋雨以后的日子慢慢拉开帷幕,而这以前的光阴似乎在瞬息间陨落,时间像烟尘一样飘渺而无有寻处。生命似乎是偶尔的一粒种子,就这样飘落人间。开花、结果、散落,由人不得。
生命,如天空的飞鸟,飞过就没有了痕迹;生命,又宛如节日里的烟花,绚烂又泯灭。所剩感怀只是已年迈的母亲曾经十月怀胎的辛苦和她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挂怀。母亲隽永执著的爱温暖着我的宇宙。
春蝶歇舞蟬才鸣
有一个阿罗汉,在一所房屋前的树下修禅入定,等他出定的时候,见房屋的女主人,怀抱着个孩子,坐在石凳上,在吃一条鱼,女人把嫩嫩鱼肉给孩子吃,自己嘴嚼鱼骨头,然后把鱼骨渣吐掉,紧围着她腿旁的一条狗儿,在地下舔吃她吐掉的鱼骨渣。这女人不时地踢狗一脚,不让狗靠太近。
阿罗汉好奇,想看看女人、孩子、狗和鱼的因缘。入定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那只鱼竟然是女人的母亲轮回转世,狗是女人的父亲轮回转世,而怀里的小孩,竟然是女人欠过命的仇人轮回转世。
这个故事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但细细想来,一点也不过分。人生颠倒,无明造业,不说是多生累劫的生死轮转,我们今生何止是噬母啖父?这也意味着,下一生的我们,何止是转鱼做狗?现在吃瓜看剧演,鱼母狗父的悲剧似乎显得很不可思议,但我们都曾吃过数不清的的鱼虾鸡鸭,羊狗猪牛?谁敢说那里面没有我们前生的父母兄弟?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眼,我们无法看清此间的因缘罢了。而当我们被孩子气破肚子的时候,我们不也直喊——不是冤家不聚头吗?人生的荒诞无稽,谁又能勘得破?恰是:
春蝶歇舞蟬才鸣
金菊花开满地黄
梧桐枝寒裹银装
白净处一滴污墨,谁也看得清
记得有一个佛教故事,有一位禅修行者,常常闭关禅坐,有一日出定时,闲步走来,到了一处池塘前,只见池水盈盈,波光粼粼,荷叶田田新绿点点,荷花正值开放,深红浅紫五光十色,随着微风,一阵清香沁人肺腑。行者正在心旷神怡地欣赏着荷花,荷花仙子飘然而至,肃然责备行者:“兄长不去修行,何来盗取我这花香?”行者吃了一惊,正要分辨,但一时语塞,竟不知从何说起。想想,也只能道歉。就在这时,那边又来一个人,看的满池的荷田,激动的手舞足蹈,以为下面肯定有藕根,跳人池中,脚踩手拔,一会儿就把新开的荷花弄了个七零八落,然后扬长而去。
行者看荷花仙子并没出来指责其人。就说:仙子,在下不过凭风借得一缕花香,就得仙子责备,而这人,掘藕残花,十分无理,仙子倒不吭声呢?”仙子笑着说:
反认他乡是故乡;
耳听八方,聚长短微妙响。
鼻闻千香,两孔洞吞霞吐雾
舌尝百味,三寸道锁龙滞虎。
身着皮囊,生生五蕴不息
意识坚强,偏偏错认了爹娘。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
今宵红綃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
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
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
保不定以后做强梁
择高粱
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唯有佛法。
因此,许多人很是仰慕那个麻鞋鹑衣,疯狂落拓的道士,希望自己有一天,看破红尘,像甄士隐一样,有一个这样的高僧来接引。岂不知,我们福报已展现眼前,佛教界出了个惊天动地大事因缘,原始古佛,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已于我们娑婆世界,真身降世,且看大日如来尊胜法王赋授记曰:
维摩尊圣,二下云霄。
法藏通达,四智圆妙。
众生怙主,无师可教。
神玄雕宝,奇端绝妙。
能取雾气,雕品定持。
展显证量,高峰绝技。
当世诸人,无圣可复。
若仿不异,我言欺世。
维摩云高,金刚总持。
佛降甘露,众见空施。
最益有情,古佛悲智。
今说示言,以证授记。”
并取法号为
仰谔益智嘎丹赤巴,
其意为
法王子至高智慧的总教主。